

大約是十年前,我購得一套由程虹教授翻譯、三聯書店出版的《美國自然文學經典譯叢》,一共四本,分別是約翰·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亨利·貝斯頓的《遙遠的房屋》、威廉斯的《心靈的慰藉》和奧爾森《低吟的荒野》。作品以優美的文學語言揭示了大自然的美麗、神秘和氣象萬千,展現了人類回歸自然后所獲得的心靈自由和內在寧靜,反思了人與自然、人類精神與自然之間一些古老但被現代人漸漸忘卻的問題,展示了作者和譯者卓越的能力與水平。當時就非常喜歡并為之震撼,仿佛一下子打通了自己通向自然文學世界的大門,在輕松的閱讀過程中完成了一次心曠神怡的審美之旅和開闊視野的求知之旅。

李克強總理與夫人程虹
巴勒斯在36歲那年辭去工作,只身到哈德遜河西岸購置了一個果園農場,并在那里親手修建了一間“河畔小屋”,繼而又在兩英里外的山間建蓋了一間“山間石屋”,在此后48年人生全部都是在這兩間鄉野小屋中度過,始終自由自在地“過著農夫與作家的雙重生活,用鋤頭和筆在土地和白紙上書寫著他的心愿”的耕讀生活,因此他的寫作總是流動著自然的聲息。譬如他寫月光下的鶇鳥:幾天前的一個夜晚,我登上一座山,看月光下的世界。當我接近山頂時,烏鶇在距我幾十米外開始唱他的夜曲。在寂靜的山野中,由地平線上的一輪滿月相伴,聽著這支曲子,此刻,城市的華麗與人類文明的自負,都顯得廉價而微不足道。(見《醒來的森林》P56)。又譬如他描寫連續兩天兩夜的森林生活:此時是下午5點,也就是說我們在森林中待了正好四十八小時。但假若如哲學家所說,時間只是現象;如詩人所說,生命只是感覺——那么,此時的我們比兩天前成熟的程度從時間上來講,且不說幾年,也有幾個月。然而,我們也年輕了許多——這有些自相矛盾,因為樺樹給我們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即它們自身的柔和與剛強(見《醒來的森林》P186)。
亨利·貝斯曾經在美國東部的科德角海灘上一座孤零零的“水手艙”住下,與大海相伴生活了一年,在這里,他聆聽著濤聲的節奏,感受海灘四季的變幻,他看到了大海的溫柔和狂暴,沙丘的包容和冷峻,這些無疑都寫進了他的《遙遠的房屋》,因而他作品的智慧經常是大海與自然給的。如關于動物與人類的關系,亨利·貝斯這樣寫道:我們由于動物的欠缺,而以施恩者自居,同情它們投錯了胎,地位卑微,命運悲慘。而我們恰恰就錯在這里。因為動物是不應當由人來衡量的。在一個比我們的生存環境更為古老而復雜的世界里,動物生長進化得完美而精細,它們生來就有我們所失去或從未擁有過的各種靈敏的感官,它們通過我們從未聽過的聲音來交流。它們不是我們的同胞,也不是我們的下屬;在生活與時光的長河中,它們是我們共同漂泊的別樣的種族,被華麗的世界所囚禁,被世俗的勞累所折磨(見《遙遠的房屋》P20)。又譬如他關于日夜變化的哲思,就這樣寫道:我們要學會尊敬夜晚并驅除對夜晚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因為,如果人類排斥夜晚的經歷,隨之失去的是一種神圣的情感,一種詩意般的意境,而這種經歷使得人類精神之旅得以擴展升華。白天,宇宙是屬于地球與人類的——是人類的太陽在照耀,是人類的云彩在飄動;黑夜,宇宙不再屬于人類。當地球放棄的白日,轉向宇宙的夜空時,不為其神秘而打動的庸俗之人寥寥無幾。在夜晚的一瞬間,我們看到了我們自己及我們的世界散布于群星之中,這是人類超越時空的永恒的朝圣。盡管這種旅行是短暫的,但在此期間,人的心靈在充滿激情與尊貴的真誠瞬間得以升華,詩意在這種人之心靈與經歷中產生(見《遙遠的房屋》P25)。

程虹教授
威廉斯的《心靈的慰籍》有一個副標題:一部非同尋常的地域與家族史。該書將其家族三代女人身患乳腺癌的悲慘經歷、美國西部大鹽湖及熊河鳥類保護基地的特殊環境聯系在一起,用一種獨特的寫作方式將人與自然之間的密切聯系展示在人們面前。關于環境致癌,她這樣道:“38歲時,我發現自己得了乳腺癌。我問醫生我應當為自己的將來做什么準備。當時的情景我依然記憶猶新。他說,‘黛安娜,我的建議是從現在起你要好好地過每一天。’醫生走后,當我躺在床上時,我在想我能活到明年送兒子上一年級嗎?我能親眼看到孩子們成家嗎?我能享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嗎?”她把目光投向遠處的湖面,她光著腳,兩腿伸開頂白色遮陽帽壓住了她黑色的短發。“一生中,我第一次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還活著。我的目標再也不是長期的規劃,而是每天的目標。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我更有意義,因為每天結束時,我都會估量一下自己一天的成果。” (見《心靈的慰籍》P132)。此外她把自己的命運與鳥類的命運連在一起:我理解母親所提到的孤寂。是它支撐并守護著我的心靈。它使我與眼前的世界融為一體。我是沙漠。我是群山。我是大鹽湖。除了人類語言之外,還有風、水及鳥述說的語言。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其他生命值得考慮:比如反嘴鷸、長腳鸝及巖石。沉靜就是從不同的生命模式中找到的希望。當我看到環嘴鷗在啄食死魚的腐肉時,我便不那么懼怕死亡。我們與周圍的生命都相差無幾。我感到恐懼是因為與整個自然界相隔離。我感到沉靜是因為置身于天人合一的孤寂之中(見《心靈的慰藉》P26)。
奧爾森《低吟的荒野》以春、夏、秋、冬四季描述了美國北部的奎蒂科-蘇必利爾荒原,筆觸優雅、沉靜、細膩,生動地喚起了人們對原野的視覺和聲音的感受。作者是這樣描寫荒野的:這種尋求荒野吟唱的行為本身就令人受益,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總會汲取人類歷史長河中的經驗,使我們感悟從簡樸的現實生活中獲取滿足的生存之道……假若我們真能捕捉到原古的輝煌,聽到荒野的吟唱,那么混亂的城市就會成為寧靜的處所,忙亂的進程就會緩緩與四季的節奏接軌,緊張就會由平靜來取代(見《低吟的荒野》P3)。
歐美自然主義流派是一個漫長的文學時期,跨越兩個世紀,期間的作家燦若星辰,程虹教授當然不可能全部翻譯這些作品,但是除了四部翻譯作品外,她還以《尋歸荒野》和《寧靜無價》兩部原創作品彌補和拓展了讀者對于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認知。《尋歸荒野》以植根于新大陸的美國神話、閃爍于自然之中的精神殿堂、拋灑在曠野之上的真實輝煌、建造于荒野之中的心靈家園和孕育于土地之中的和諧與美等五個章節,介紹了史密斯、布雷德福、愛德華茲、巴特姆、小巴特姆、威爾遜、科爾、愛默生、梭羅、惠特曼、巴勒斯、奧斯汀、利奧波德、迪拉德等更多一批自然主義流派的作家。程虹教授在譯介西方自然主義文學流派作品的同時,顯然也提升了自己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在《尋歸荒野》中她這樣寫道:我們需要荒野,無論我們是否真正走進它。我們需要一個避難所,盡管我們永遠也不必去那里。比如,或許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不會去阿拉斯加,但是我對它的存在心存感激。就像我們需要希望一樣,我們需要躲避的可能性;沒有荒野,城市的生活將會把所有的人都逼進犯罪、吸毒和瘋狂的深淵。《尋歸荒野》出版于2001年,二十多年前,在整個中國,對荒野有如此深刻認識的人當屬鳳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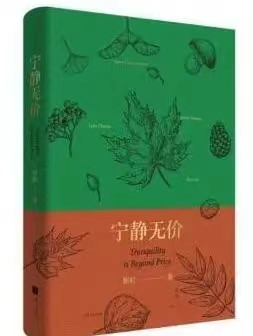
程虹教授著《寧靜無價》
由稍后幾年出版的《寧靜無價》一書,程虹教授不僅深入觀察美國自然文學作家群、女性自然文學作家的興起,而且把目光投放到歐洲,關注從18世紀到20世紀的英國自然文學作家的譜系,也更多融入到自己對當今社會的思考,對人類永恒主題的思考,深刻闡述了寧靜是尋求自我本真的過程,因而更富有現實意義。實際上這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已經著重注意了自然主義文學流派對西方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的制定,譬如他在講述寫作《夏日走過山間》自然主義文學作家繆爾時寫道:1903年春,繆爾陪同當時在任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瀏覽了優勝美地山谷。羅斯福和繆爾消失在山谷的樹叢里,在那里度過了周末。盡管對于他們的會面沒有公開報道,但從后來發生的事情來看,許多羅斯福關于自然保護的策略,或許就是從那時,在繆爾的勸導下開始設計的。這促使羅斯福成為一個“不是為了我們眼前的利益,而是為了國家長遠利益而建設這個國家”的總統。
如果繆爾一次偶然的山地之行就如此深刻地影響了羅斯福總統關于自然保護的策略,那么程虹教授的身份更能給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帶來更大的影響和賦能,當然這只是揣測與臆想。但是她的譯介打通了我們通向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大門,我們這一代的很多讀者都受到其作品的影響,這些作品深厚的博物學知識和自然主義精神,讓我們深受裨益。感謝程虹教授,給了我們很好的閱讀文本。
作者:黃亮斌
來源 :湖南生態文學分會
